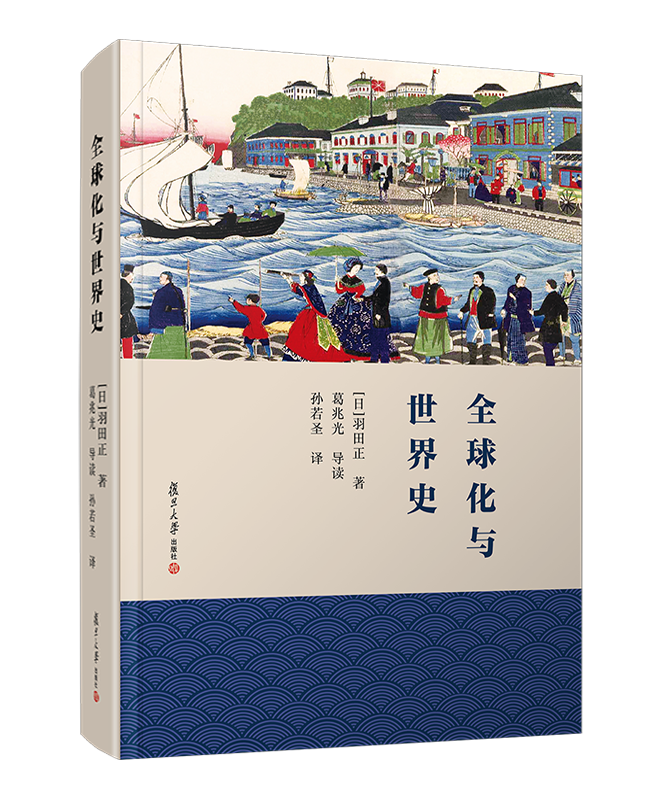
《全球化与世界史》
[日]羽田正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自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的风格,日本独立于西欧、东亚,在世界史的框架中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格局。东京大学羽田正教授将其归纳为“全球史”的日本视角,然而,这一保守的文明区隔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日本人强大的民族认同,却掩盖了另一重复合的“地球公民”身份确证的可能。
在《全球化与世界史》一书中,作者羽田正主张世界上的人们需要保有强烈的“地球居民”意识,相互协作,以应对当今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等课题,并提议朝着这样的方向重新思考对世界史的理解与叙述。羽田正认为,正是在难以实现世界性的协调态势的当下,本书可以在已成长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出版才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羽田正先生近影
新冠传染病大流行中,世界作为整体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疾病肆虐期间,政府间的合作似乎并未如预期般展开,但民间层面出现了暖人心脾的交流。比如2020年1月末2月初,日本的民间团体向中国输送了包括口罩在内的医疗用品等大量支持物资。装载物资的箱子上写着“山川异域,日月同天”,触动了中国人民的心弦。
之后经过了两个月,日本的感染情况愈发严重,商店里的口罩发生断供。虽然政府呼吁民众佩戴口罩,但是民众根本无处求购。危机之中,是中国人民向日本送来了大量支援物资。作者供职的东京大学也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众多慈善人士及友好人士的口罩。身为东大执行副校长的羽田正先生作为校方代表接受了支援物资,他表示:“我确信在民间层面,人们完全可以作为地球居民,超越国境进行交流。”
《全球化与世界史》导读
文/葛兆光
引言:思考世界史研究的“暗默知”
历史学家的职业,就是回顾以往的世界、国家和人们走过的路,所以,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一定会追根究底,不仅追溯历史本身,而且追溯历史叙述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当他反思历史的时候,也质疑形成历史论述的基本依据:第一,为什么历史是这样变化而不是那样变化?第二,为什么历史要这样论述而不那样论述?第三,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个历史论述,而不相信那个历史论述?
英国的历史学家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在《自传》(An Autobiography)中,就曾经用比喻来批评某些学者,说他们总是不提供有关历史论述的根基,这就如同告诉读者“世界放置在一头大象的背上。但他希望人们不再追问,支撑大象的东西是什么”。有意思的是,这个比喻和中国宋代理学家程颐的故事很接近,《伊洛渊源录》中记载程颐面对着桌子思考时,也向他的老师问了追根究底的问题,“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大地安在甚处”。不过,和科林伍德所说的那些历史学家不同,据说程颐的老师给了他答案,也给了他启迪。
我读日本著名学者羽田正(Haneda Masashi,1953-)教授的《全球化与世界史》时,就感觉到,当一个历史学家开始反思,而且这种反思不只是针对历史,更是针对历史论述的根基的时候,他就不得不追问“支撑大象的东西”或者“大地安在何处”,同时也不得不对过去习以为常的历史论述,作一番重新检讨。在写这部书的时候,我想,羽田正所面对的,不止是日本从明治、大正、昭和、平成以来百余年的学术积累,他也不得不面对十九世纪以来全球的现代历史学传统,甚至还要重新检讨当前,也就是二十一世纪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预设。
在书中,他把这个安放大地或支撑大象的“基本预设”,叫作“暗默知”(あんもくち),在中译本中,这个词被译成“默会的知与识”。我查了一下辞典,“暗默知”在英文中是tacitknowledge,也就是我当年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中说的“不言而喻的预设”。据说,这个词是一个叫波兰尼(Polanyi)的学者在1958年提出来的。不过,羽田正特意解释说,暗默知不仅有“知识”(knowledge),还有“意识”(consciousness),也就是说,这个“暗默知”应当是在所有的知识、经验和直觉之下,支撑着一切理解的前提。这个安放大地或支撑大象的东西,也许在哲学家看来,似乎有点儿像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所谓的“前理解”(Vorverstandnis)。
那么,在羽田正面对的世界史研究领域中,他觉得需要反思的“暗默知”是什么呢?
一、在全球化背景中: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的处境
正如书名《全球化与世界史》所显示的,羽田正思考世界史的问题意识,首先与当下的全球化趋势有关。
当然,现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经出现了种种问题,2020年这次疫情也凸现了全球化的困境,甚至有人预言,一个“逆全球化的时代”即将到来。但是无论如何,从十五世纪以来的近五六个世纪,仍然可以看作全球化的时代,因为在历史学家看来,全球化首先就是一个历史过程。按照我的理解,如果说十五世纪的大航海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那么,从十六世纪中叶欧洲传教士来到日本和中国,东亚就逐渐被整编到早期全球化历史过程中了。
在这个漫长的全球化历史过程中,同在东亚的日本,比中国更加迅速地融入世界,也许,这是因为日本并不像中国那样,对异文明有“整体主义”和“改造主义”的传统,日本的“受容”和“变容”往往采取实际态度的缘故。无论是早期接受汉唐宋的华夏文化,还是十六世纪后期相当令人震撼的天主教皈依潮(当然也有后来的禁教),无论是流行实用的南蛮医学或兰学(当然江户时代还有更重要的程朱理学),还是也可以叫做“睁开眼睛看世界”,如新井白石(1657-1725)的《西洋纪闻》、《采览异言》和西川如见(1648-1724)的《增补华夷通商考》。
我们看到早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就曾积极地拥抱世界,这一点似乎比中国、朝鲜和越南更迅速更顺畅。尽管明治时期也有过“脱亚入欧”和“亚洲主义”的一波三折,二战时期也有过所谓抵抗欧美和倡导“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潮,但总的来说,这一百多年里,日本显然比中国更愿意融入源自近代欧洲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在如今,这个全球化(日本通常用“グロ-バル化”直接翻译英文)对于日本来说,似乎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确实是这样。作为曾经担任日本首屈一指的东京大学主管外事的常务副校长,同时也作为一个深知国际学术资讯的世界史学者,他在书中列举的若干日本学界的现象,就说明日本——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在面对全球化的潮流时,都曾经试图大力推动日本科学与人文的“国际化”。而为了这种“国际化”,日本政府和有关机构也曾使出浑身解数,包括推动大学的国际排名,争取更多的诺贝尔奖,增加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话语影响。这在日本似乎已经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共识。但还是让我有些吃惊的是,羽田正在书中提到,日本官方居然会发出“我国大学全球化的迟滞程度已达危机”这样的严重警告,而著名的学术振兴会,甚至罕见地直接指责日本的人文学者,“在当今国际化的时代中,大多数研究者不能自如运用英语(或相应的语言),这一现状乃是我国人文科学的致命弱点”。日本的这种似乎不能融入全球化,就等于自绝于世界的危言耸听,看上去是那么焦虑和紧张,这让我想起当年中国曾经流行过的“落后就要挨打”和“会被开除球籍”等言论。
可问题是,全球化就是国际化?国际化就是西方化?日本人文社会科学如果要进入世界知识系统就必须用英文(或相应的语言)写作?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难道一定要有和西方学界一样的问题意识和论述策略?显然,羽田正对于全球化,尤其是日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追求的国际化趋势,保持着冷静的思考立场和批判态度。我与羽田正有十几年的交流,据我了解,他是一个坚定的世界主义者,他当然知道全球化时代,人们必须超越国界去思考,也当然知道人文社会科学,确实需要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共通的问题意识,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融入国际语境,这也就是中国学者熟悉的所谓“预流”。不过,同时他也特别警惕,为什么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国际化,就是欧美化?为什么这个国际化,不是他化过来,而偏偏是我化过去?为什么日本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能用日语表达日本的思考,而一定要用英文?换句话说,就是这种人文学术的全球化趋向,会不会使得日本从此失去“主场”,也失去自己的“言说”?
更何况,欧洲人文社会科学本身所包含的“暗默知”,也就是需要反省的思考前提,其实存在偏见,未必那么适合“世界公民”或者“地球居民”。那么,为什么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一定要完全接受它呢?具体到世界史研究来说,就是当日本学者在撰写世界史的时候,他怎样才能避免来自欧洲学界的“暗默知”,使得这个世界史既有全球的视野和世界的眼光,又具有日本学者和日本语言才能呈现的论述立场和问题意识呢?
二、暗默知:人文学术难以回避的前提
在第二章里,羽田正曾提到他的一次经验。
2015年他在德国某大学参加为了“Excellence Initiative”(卓越创造)计划而召开的全球有识之士座谈会,他注意到,德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科分类表分成五列。其中,第二列是“文化人类学,印度学及比较宗教学,中国学,朝鲜学,日本学,伊斯兰及东方学”;而第三列是“古代史,中世史,近世史,近代史,地域史,东欧史”。这表明,在德国同行的心目中,“本国与‘欧洲’的相关研究纳入一个体系,并将该体系与‘非欧洲’相关的研究,明确地进行区分,而这种区分最终形成了学科领域二元对立式的体系化”。羽田正把德国这种学科体系与日本进行了比较,众所周知,日本从明治时代那珂通世(1851-1908)提议之后,历史学已经形成“本国史”“东洋史”和“西洋史”的三分天下,尽管东京大学历史学科以及现代日本的历史学,从一开始就深受德国学者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ess)的影响,但毕竟东京大学是日本的大学,所以,它还是形成了和德国不同的历史分类,而在这两个不同的历史分类背后,就有欧洲和日本各自都未必自觉的“暗默知”。
学科分类本身的意义,就是为了给知识建立秩序,而建立知识秩序的背后,则是提供思考的价值和等级。以前,米切尔·福科(Michel Foucault,1926-1984)就曾经在《词与物》的前言中,以一个据说是他杜撰的,即所谓赫尔博斯“中国百科全书”(unecertaine encyclopédie chinoise)的动物分类,说明不同文化就有不同的知识秩序和观念基础。也许,正是因为德国(甚至整个欧洲或西方)学术有这样“欧洲vs非欧洲”的这种“不言而喻的前提”,所以,如今欧美各个大学才有那么特别的“东亚系”。人们很容易注意到,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西方各大学里,往往是东亚的历史不在历史系,东亚的文学不在文学系,东亚的思想不在哲学系。羽田正在书中就列举了美国耶鲁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以及亚洲各大学的“亚洲研究”,指出这些大学学科的分类背后,其实,都有各自区分“自我”和“他者”的意图。
显然,学科分类并不仅仅只是为了院系分类。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欧洲vs非欧洲”的分类,又带来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中心与边缘这样的价值区别。正如羽田正所说,“对于当时西欧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所属的‘欧洲’这一空间,包含了他们所信仰的所有正面价值观,如进步、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与此相对,‘非欧洲’则充斥着诸如停滞、不自由、不平等、专制、迷惘等负面的价值。两者虽共存于地球上,但是两个完全异质的空间。(由于)当时西欧国家陆续对非欧洲国家进行了军事征服与殖民统治,这一事实似乎可以为这种二元对立世界观的正确性进行背书。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群体,存在毫无理由的优劣之分,其中‘欧洲’人在所有方面都优于‘非欧洲’人”(第二章)。
具体到世界史的叙述,由于这种“暗默知”不仅包含了知识分类,而且隐含着价值等级,同时也涉及历史叙述的中心和边缘等潜意识或无意识,因此,过去的世界史,常常就是以欧洲为中心,以近代欧洲观念中的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传统与现代变迁为主轴,也是以历史上欧洲社会的发展阶段的模板为典范来书写的。甚至在历史叙述的概念上,那些从西方语言翻译过来的概念,也会裹挟着来自近代欧洲的知识论和价值观,重新切割和组合着包括东方和西方,也包括了日本的世界历史,这使得十九世纪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以来的世界史,无论它如何变化,它的底色仍然只是以欧洲中心的世界史。
不过,羽田正又说回日本。他说,“在西欧各国形成体系化的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在进入日本后,以‘自我’和‘他者’的转换为轴心,逐渐本土化,并孕育出了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独特的性格”。作为日本学者,羽田正为明治以来的日本历史学传统进行辩护说,日本与德国不同,“日本在如何看待理解世界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与德国及西欧殊异的,独特的暗默知”(第二章)。由于日本的人文科学意识到“自我”是“日本”,除此之外无论是东洋还是西洋都是“他者”,此处并没有“欧洲”之于德国那样的另一个“自我”,在日本认知中的“他者”,“欧洲”与“非欧洲”各占一半,也就是“西洋史”和“东洋史”,所以,日本的世界史领域因此避免了“欧洲vs非欧洲”这样的尴尬问题。特别是在亚洲研究领域,他说,由于日本学者把亚洲研究的对象,设定为除了本国以外的所有亚洲地区,所以,他们可以立足于日本,观察世界特别是亚洲。这种独特立场,就源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的日本式世界历史认知,也就是把世界分为日本、东方与西方这种历史三分法。
也许这有道理。但是,这里我也有一些疑问:第一,这种历史三分法,也就是把历史分为本国史、东洋史、西洋史,难道没有另一种“暗默知”吗?第二,这种把本国看做“我者”,把“西洋”和“东洋”看成两个“他者”的“暗默知”背后,难道没有难以察觉的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念吗?第三,它真的凸显了“世界上所有区域都具有相同的研究价值这一认识”吗(第五章)这一认识吗?
这是我想继续和羽田正教授讨论的问题。
三、如何超越国境:重建全球史/新世界史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新世界史或全球史,羽田正教授是近年来日本“新世界史”的提倡者,特别是近几年,他的很多著作都在谈论“新世界史”。
如前所说,从十九世纪的兰克以来,逐渐形成了以欧洲为重心,以近代欧洲价值尺度为尺度,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单位组合的世界史模式。对于这种世界史,羽田正在另一部著作《新しい世界史へ――地球市民のための構想》中,已经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本书第五章《世界史谱系与新世界史》中,他再次提及这些批评,在他看来,日本目前通行的世界史有三个缺陷。第一,现行(日本)的世界史是日本人的世界史,也就是说它只是从日本角度去看世界;第二,这些的世界史强调“自我”“他者”的区别与差异,也就是说,总是有一个现代国民国家的框架;第三,现行的世界史并未摆脱欧洲中心史观,包括欧洲中心的价值尺度。
这种批评都很有道理。以现代国家(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为单位的历史叙述,有时候会捉襟见肘,因为某些历史事件放在更大视野中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很难解释的矛盾。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作“顺理成章”,原本在一国史或者单线的世界史中,那些看起来“顺理成章”的历史解释,放在全球史/新世界史视野中,却出现理解和解释的歧义,并不“顺理成章”了。原因就在于原来的“理”,可能并不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古人所说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如果不超越国境用全球眼光来看,其实未必可能。近来,我曾经就用清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盛典为例,说明同一事件在中国史、亚洲史和世界史的不同背景中,会有相当不同的理解和评价。而羽田正也在第八章《全球史的可能性》中,举了一个相当有趣的例子,他参加一个博士生论文答辩,这篇论文以福科《规训与惩罚》的思路,批判殖民主义,讲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埃及,作为监狱总监等职的英法外籍官员,不顾当地埃及人反对,强行引进了西欧制度,这种外籍官员在埃及史中,显然是殖民者的负面形象。然而,这一论述让羽田正联想起日本,就在同一时代,许多西方人作为“外籍雇员”在日本政府任职,他们也同样把西欧及北美的政治制度引入日本,可是,这样做的法国人布瓦索纳德(Gustave Émile Boissonade,1825-1910),在日本甚至被尊称为“日本近代法之父”。他追问道,如果是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历史,这两个同类事件的两个不同评价,似乎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在超越国境的全球史中,它该怎样理解和解释呢?
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建筑未必有特色,历史也未必那么悠久的长崎天主教堂群,凭什么值得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位于西北中国的敦煌和麦积山石窟在14-17世纪的修复,可以算明代中国的事业吗?德国历史博物馆关于“在欧洲中的边界(border)”解说中,有关“德国”、“历史”与“国境”的说法,是不是可以祛除“自古以来(就有日本)”的暗默知?在第八章中,羽田正列举了好些例子,说明无论在价值观念、历史论述和疆域变迁等问题上,拘泥于“现代国家”立场和遵循“世界视野”的历史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历史究竟应该怎样论述?这确实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知道,由于十九世纪世界史形成的时代,正是民族国家或者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历史书写的意义可能主要是在凝聚认同和确立国家,因此这种历史叙述,哪怕是整个世界史的叙述,也必然是默认世界上各个现代国家从传统帝国蜕变出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并且在这样的历史观念下进行历史叙述的;可是,正如我在“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导言中所说,“历史学总是有两个崇高理想”,凝聚认同和确立国家的理想只是其中之一,“也就是通过国别史追溯民族和国家的来龙去脉,让人们意识到,我们是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流着同样的血,有着同样的历史”。然而,历史学还应该有另一个崇高理想,这就是培养地球居民的共同意识。正如羽田正所说,现在是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纪,不同于主权国家的二十世纪,这个时代的全球史或新世界史,希望培养我们所说的“世界公民”。顺便可以说到,“世界公民”,或者Global Citizen这个词,羽田正仍然觉得不足以表达超越国家、民族和地域的意味,特别是在日语中,与citizen对应的“市民”仍有其微妙的差异,所以,他宁愿接受美国学者的建议,把它称为residents of the earth(中文译本把它叫作“地球居民”,见第五章)。而现在的全球史或新世界史,它的意义就是为了“唤起人们作为地球居民的意识”(第七章)。
那么,全球史或新世界史怎样才能“唤起人们作为地球居民的意识”呢?羽田正指出,在传统的世界史中,“世界被视为由国家及若干个国家聚集而成的地域或文明圈构成。这些国家和地域各自拥有基于时间轴的自身历史,把这些历史合并起来归结为一个整体,就是世界史”。但是,羽田正设想的新世界史却接近如今盛行的全球史。显然,羽田正很认同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在《全球史入门》中的意见,康拉德在第一章《导论》中,曾把传统世界史的缺陷归结为“内在主义”和“欧洲中心”,一方面是世界史的起源,与国民国家具有深厚关联,另一方面是世界史深陷欧洲中心论,他把它们称为“(世界史的)两个胎记”,也就是世界史与生俱来的两个缺陷。因此康拉德主张,Global history正是解决近代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不幸特质的有效且独特的路径。而羽田正说,“康拉德的见解和提案,在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的框架中,完全具备可接受的价值”(第七章)。所以,他也把新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对象和目标,设定为以下三点,(1)为地球居民培养全球意识,(2)破除某种中心主义,无论是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东方或日本中心主义;(3)超越国境,强调历史联系,即“一直以来被忽视的关联性和相关性的存在”(第五章)。
为了这样的新世界史叙述,他觉得新世界史应当努力描绘某个时代的世界全景图,不必拘泥于按照时序书写的历史,强调横向关联的历史。我想,这正好就是如今国际历史学界的趋势。不仅德国学者康拉德这样说过,英国学者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什么是文化史?》中也这样说过,“未来历史学研究的趋势之一,可能是‘文化接触’,即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接受与转移、边缘对中心的影响,以及从边缘重思世界历史”。我当然完全赞同这个想法。全球史或新世界史最应当做的,就是在寻找整个历史里这种潜伏的、有机的、互动的关系,其实,历史的关联并不都那么神秘和诡异,一个好的全球史或新世界史学者,必须有意识地发掘这种关联性,因为新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学者总是希望,让读者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自古以来我们互相就有联系,我们要学会共同生活,成为“地球居民”或者“世界公民”。
问题只是,作为历史学家,他面对的具体学术问题是,历史叙述不能散乱,它必须有某种清晰的脉络,那么,全球史或新世界史如何把漫长时间里全球范围繁多的联系和接触,放置在井然有序的历史框架内,呈现出时间和空间的交错?也就是不仅有纵向的清晰的时代变迁,又有横向的丰富的全球联系,就像羽田正所说,把历史书写成有经线和纬线的“织锦”呢?
四、全球织锦:经线与纬线
让我简单提及英国史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
我一直非常佩服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他对历史不仅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在历史叙述上有精准的概括力。他用“革命”(1789-1848)、“资本”(1848-1875)、“帝国”(1875-1914)和“极端”(1914-1991)四个高度概括的关键词,清晰地梳理了法国大革命至今的四段历史,让人一眼就看到历史的变迁轨迹和历史学家对历史重心的把握。不过,在“年代四部曲”中,霍布斯鲍姆讨论的重心,还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我始终在猜想,如果他还在世,对于更广阔的全球历史,他会用什么样的角度和词语,来概括更复杂和更宽广的世界历史变迁?
在羽田正的这部书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当然,尽管它只是尝试,而且相当简略,但已经很有启发。在第五章《全球史谱系与新世界史》里,他对日本通行的世界史模式进行反省,他认为在这个模式中,“(各个)国家和地域各自拥有基于时间轴的自身历史,把这些历史合并起来归结为一个整体,就是世界史”。这也就是前面说的,过去的世界史往往就是各国历史按照时间顺序的组合。而贯穿这个纵向历史的主轴,则是“16世纪以后欧洲或者说‘西方’地域开始经略世界各地,世界在‘西方’的主导下,开始推进一体化”。但是,羽田正觉得,新的世界史不能够被这个脉络绑架,而是应当在时序的纵向脉络之外,另外设计交错的横向联系。他说,“试将‘世界史’当作一张纺织品。那么,时序史是‘经线’,而我的提案则是‘纬线’。相对于积累到相当程度的经线而言,……应当在修补经线漏洞的同时,用心强化纬线。随着纬线被顺畅地编入,想必一定会呈现出美丽的新图案”。
我完全赞成这个想法。就像一幅织锦需要经纬交错一样,世界地图上也必须有南北纬线和东西经线,而理想的世界史或者全球史,当然更希望兼有时间与空间。但是,仅有理想是不够的,理想必须有落实的方案和途径。世界太大,历史太长,线头太多,历史学家如果不能像霍布斯鲍姆那样,从丰富的历史中拈出“革命”“资本”“帝国”和“极端”这样的关键词,将丰富的历史提纲挈领,然后纲举目张,历史将成为一团乱麻。全球史或世界史的难处就在这里。然而,羽田正在第九章《为推进新世界史描绘的四张全景图》中,选出1700年、1800年、1900年和1960年这四个座标性年代之后,用非常精彩的帝国史或新帝国史的眼光,对这几百年的全球史作出了交错贯穿的尝试。他在这里,再次批评了通常以西方中心的世界史,他认为,那种“欧洲”与“非欧洲”对峙的“暗默知”,它不是全球人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世界史,无法解释和概括丰富的历史世界,而希望在通常的“经线”之外寻找“纬线”,也就是绘制“某个时代的世界全景图,通过全景图与现代的比较,可以对现代世界产生更深入的理解”。
问题是,1700年、1800年、1900年和1960年,在全球史或者新世界史中,它们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能够贯穿起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欧洲或者日本的历史,同时日本(或者其他区域和国家)的历史,又能够恰如其分地被安置在这个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经纬线中,得到贯通的解释呢?
五、四张世界史图:旧帝国和新帝国
让我们来看一下羽田正作为世界史“纬线”的四幅图像。
第一幅:“帝国、王国和小共同体共存的时代:1700”。
羽田正用帝国的统治与支配、宗教与政治合法性、民众构成与社会结构、认同与归属、语言等要素,描述1700年前后的世界历史横断面。他指出,1700年前后的世界上,存在各个庞大的帝国,“从东开始依次是清帝国,莫卧儿帝国,萨菲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及哈布斯堡帝国”,也存在着各个王国,例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格兰、尼德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意大利半岛的周边地带的一些王国。这些帝国和王国的共同之处,首先在于多种多样的人生活在帝国的统治之下。但是,这些帝国或王国内部的民众无论在语言、宗教、生活习惯、价值观、归属意识上都有差异,不同的族群交错地共同生活在一起,他们并没有“国家认同”。而帝国或王国的上层,也由各种复杂的贵族构成,皇帝或国王的权力及正统性由宗教确认,而皇帝也充当宗教的保护人,有时候皇帝或国王还会充当不同宗教,甚至不同族群的代理人,像清朝皇帝就同时是儒佛道的代言人和满蒙回藏汉的统治者。帝国并没有固定的疆域,皇帝们“在理念上并非以现有疆域为对象,而是带有普遍性地辐射到更远的四方,就神圣罗马帝国的两个继任者哈布斯堡及俄罗斯帝国而言,这种理念并非难以理解,清帝国同样认为自己皇帝的德行泽被着整个世界”。但是,在这样的世界中,欧洲的王国英格兰和法兰西“实行将支配领域内部的政治统一(王权强化)与宗教统一相联结的政策”,逐渐趋向中央集权这种政治方向,这种方向在不知不觉中更进一步,走向了主权国民国家。而在这样的世界历史语境中,回头来看日本,当时的日本,逐渐形成把荷兰人、中国人、朝鲜人、阿依奴人视为他者,把日本列岛的人视为日本人这样的自我认识与世界认识,并且形成以“神佛习合”为特征的共同信仰,似乎与同时期欧洲的英、法相似。因此,羽田正认为,在世界史中看日本,似乎那个时代已经初具主权国民国家的雏形。
第二幅:“帝国变动的时代:1800”。
在1800年前后,大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在中亚角逐,莫卧儿和奥斯曼帝国在衰落中,哈布斯堡帝国卷入与普鲁士和法国的争斗,各个帝国疆域发生了变化,有些帝国甚至已经衰亡,但帝国这种政体依旧在欧亚大陆发挥着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出现了两种新的政体,一是英法等主权国民国家,二是美利坚合众国。现代主权国家(或国民国家)的兴起,促成了国族认同意识。国民国家的统治正当性不需要宗教来进行保障,从这点可以看出,它与帝国的巨大差异。同时,一百年前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小共同体,逐渐不复存在,它们都被置于英、法、俄、清等强大政治体的支配下。而在1700年,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这就是从1700年到1800年前后,世界史发生的重大变化。
第三幅:“旧式帝国与国民国家竞争的时代:1900”。
按照羽田正的说法,到了1900年前后,世界变动的规模远远超过前两百年。变动可大致理解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由于国民国家兴盛导致的旧式帝国的困境;第二类是与国民国家兴盛相关的新式帝国诞生。前面一类,包括四大传统帝国,如俄罗斯进行了农奴改革,清朝开展洋务运动,哈布斯堡变革为奥匈帝国,奥斯曼颁布了旦泽玛特宪法。由于帝国包含了不同族群与不同信仰,现在刺激出了新的归属意识,所以帝国遭遇统治的麻烦;也由于国民国家比传统帝国在政治与社会管理上拥有优越性,促使这些传统帝国也被迫在艰难转型。后面一类,比如英法德日等国民国家体制在逐渐完善中,由于它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幅度增强,与这些国家作战的传统帝国逐渐处于下风,它们成为了新式帝国。
在书中,羽田正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从现代国民国家发展出来的新帝国,就像核心有蛋黄的荷包蛋,蛋黄是同一性的国民国家,蛋白则是它们的殖民地;而传统的旧帝国则像蛋黄和蛋白被搅在一起的炒鸡蛋。“因为(旧帝国)其基本的统治构造,是在统治中心并不存在明确的族群支配集团,蛋黄和蛋白不加区别地被搅合在一起”。在新式帝国和旧式帝国的竞争中,传统的旧帝国逐渐衰亡,只有俄罗斯和中国,仍然保存了庞大的疆域和复杂的族群。而恰恰是这一旧帝国传统的延续,给这两个庞大的帝国带来了此后的种种问题。“190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一方面旧帝国企图通过改革维持其统治体制及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新帝国在互相争斗中,将触手伸展至世界各个角落,将各地作为自己的殖民地”。而在这个世界史背景中,日本正好就是经由国民国家转向了新式帝国,如果说在东亚各个国家中,那时的日本似乎是一个例外,但在整个1900年前后新式帝国与旧式帝国角逐的世界史中,日本又不是一个例外。
第四幅:“现代的国际秩序与主权国家:1960”。
经过六十年,世界历史又发生变化,近200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象征着现代国际秩序和主权国家构成了世界。羽田正再次用鸡蛋作比喻,他说,表面上看,这近200个主权国家都成了“蛋黄”,即当时盛行的“民族独立”所建立的国民国家,而“蛋白”已经不见了。不过,世界并没有形成普遍的和同一的现代国家。其中一种,是传续着“炒蛋”式传统帝国的苏联、中国(还有情况不太一样的印度),虽然建立了形式上的国民国家,但它主要依靠的,一方面是设置半独立的共和国(苏联)或者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国)来缓解族群矛盾,另一方面是用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维持国家正当性和国家认同。而另一种呢?即使是形式上是同质化的现代国家,但其内部的认同仍然存在差异。表面上它从过去的附属殖民地已经转型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但内部国民由于族群、宗教、经济和文化之差异,并不具备同一的“国民”意识。其中一些国家沿袭了殖民时期的国境,而这国境却并不与族群、宗教、经济与文化叠合。所以,尽管现代世界越来越全球化,但是事实上差异仍然存在,并成为世界互相融合、彼此接近的障碍。羽田正在这一节中,描述了追求地域统合的欧洲、作为新帝国的美国、问题重重难民众多的非洲与中东,与全力维护安定与秩序的中俄之后,又回头说到日本,“日本与其他国家一样成为了主权国民国家。这个国家的国民保有二战战败的共同回忆,从语言、宗教、习惯等人类文化环境的均质性来看,日本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典型的国民国家”。
这四个世界史的横断面,相当精彩也很有概括力。但我还有一点儿心存疑虑,我想到的问题是,当我们使用传统帝国、新帝国、民族国家或现代国民国家等,作为历史关键词,来梳理和整合1700年以来的世界史或全球史,背后是否仍然还会有欧洲或西方的观念阴影呢?
结语:对新世界史或全球史的期待
“学者若不为理想奔走疾呼,则世间理想之声殆矣”(第五章)。
当我看到书中这句话,心里非常感动。我知道,羽田正对“新世界史”这个理念的普及和推动,自有他自己的特别关怀。羽田正的祖父是日本最著名的东洋史家、担任过京都大学校长的羽田亨(1882-1955),虽然他一直坚持说,自己没有家学渊源。但是,从羽田亨以来越出日本国境关怀整个亚洲的学术传统,也许,曾经影响了他的专业选择和历史视野。自从2008年我和羽田正教授、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一起,开始推动复旦大学、东京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三校合作的时候起,我就逐渐理解到,他始终在追求超越国境的大历史叙述,也始终在促进日本的“地球居民”意识。也许,二战之后出生并且在二十世纪后半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都会有一些关于世界主义的理想,也都有一些面对全球化的焦虑。这些年,我常常有机会和他交谈,我想,如果读一读这部《全球化与世界史》,我们可以看到,羽田正教授作为杰出的伊斯兰世界史专家,也作为日本东京大学学术与行政领导人之一,面对目前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不得不适应全球化的日本学术,显然他有他的理想,也有他的深刻思考。
我对于羽田正所提倡的新世界史或全球史,当然抱有深切而热烈的期待。不过,作为一个中国的历史学者,也许和日本历史学者的关怀各有偏重,我在积极支持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同时,也同时提醒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立场叙述全球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许,这里也有来自中国的“暗默知”吧。我在“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导言”中曾经说到,没有哪一个全球史家可以宣称,自己可以全知全能,会360°无死角地看历史。几百年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在《职方外纪》里曾说:“无处非中”。当你明白这个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就没有哪一个地方,可以宣称自己是“中心”,但是,于此同时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也都可以宣称自己是“中心”。在十七世纪,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前一半意思,颠覆了古代中国固执的“天圆地方,我在中央”的观念,也带来了一种多元的世界观。可是反过来,如果把后一半意思用在全球史或新世界史上,那么,全球史或者新世界史的写作,就一方面要破除单一的中心主义,要承认历史是多元的、复杂的、联系的,另一方面也要破除历史学家傲慢的全能主义。我们的历史学家别以为自己能够全知全能,要承认自己不是千手千眼观音菩萨,我们只能或者更能从某一个角度(中心)看世界。
所以,中国学者看全球史,也许和从美国看全球史,从欧洲看全球史不同,也和从日本看全球史不同。所以,我才把我参与策划的全球史计划,命名为“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我希望的是,有各种不同视角不同形式的全球史,直到我们达成共识,并且有能力把这些全球史总和起来的时候,我们才有了一个多个角度观看、多种立场协调的“全景式全球史”。我很高兴地看到,羽田正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特意为此修正了过去对“日本人的世界史”的批评,觉得这种世界史“并非致命的缺陷。因为目前尚不存在被地球上所有人所共有的世界史,并且这样的世界史也并非目下亟需之物”(第五章)。我想,也正因为如此,羽田正在强调普适性学术研究和世界性学术课题的同时,也同时提到日本学界和日语论著的重要性。这种站在日本的“主场”,又超越日本“视界”的理念,以及用这样理念撰写为“地球居民”的新世界史论著,进一步重建为全球的人文社会科学,其实,也正是日本学界和中国学界所需要的共同理想。
最后我要说,羽田正《全球化与世界史》这部著作篇幅并不大,但涉及面相当宽。这部书从日本学界面对全球化时代,如何寻求国际化的焦虑开始,讨论了当今世界人文学术背后的“暗默知”,提出了知识多元化与语言问题,然后进入他所熟悉的世界史的讨论。在世界史的讨论中,他不仅提到新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写法,并且现身说法,提供了有关1700年以后世界史的四幅图景。我个人感受最深的,其实还是书中关于如何超越国家、族群和个人局限的想法。我感觉到,羽田正始终在追问人文社会科学的“暗默知”,也就是反思全球化时代人文社会科学背后那些被无意忽略的预设或前提,不断地在追问它,真的是绝对正确的吗?同时他也在追问,谁来提供世界历史的叙述脉络,现在的世界历史叙述能适合未来地球居民的认识吗?新世界史或全球史在打破了传统的前提或预设之后,“安放大地”或“支撑大象”的又是什么呢?
中国哲人庄子曾经感慨,“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进入二十一世纪,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好像已经如庄子所说的那样“道术将为天下裂”,尽管地球越来越小,可是知识、价值和理想却渐行渐远。那么,通过全球人文社会科学,通过新世界史或全球史,能不能让人类意识到:我们将是“地球居民”,而作为未来的地球居民,我们能不能共享世界,学会平等相处,而且找到共同的“道”呢?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