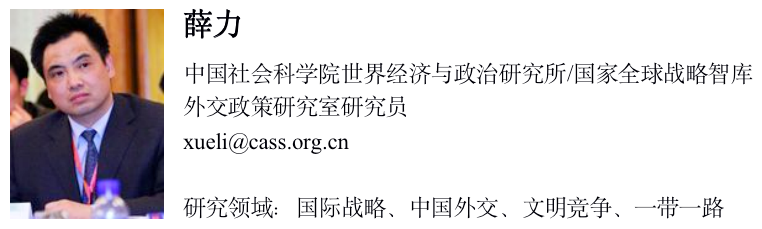
美国主观上不愿意、客观上无能力且不被接受继续承担领导世界的角色与成本。美国的文明影响力在下降,这是一个主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整体而言,美国表现得越来越不像一个世界领导国,而像一个普通大国。
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科技水平等指标看,美国依然是超级大国。但是,世界正在进入文明竞争的长周期,从文明竞争的视角看,美国正在从超级大国“回归”普通大国。这一过程,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初步成型于特朗普时期。拜登整体上延续了特朗普主义。2030年前后,美国有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普通大国”
成为超级大国需要主客观两方面条件:主观上有意愿;客观上有能力且国际社会也能接受。这里的能力指综合能力,主要包括:一套新的外交理念与执行这套理念的外交人才、对国际机制的构建与把控、超强的经济实力、领先的教育与科技水平、强大的军事能力与全球军事同盟体系。从文明竞争的视角看,则要求一种文明的全球影响力明显高于其他文明,不但客观上具有压倒性优势,主观上也愿意将这种优势操作化。二战后的美国是典型例子。
一、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时代背景
救世主情节是一神论基督教的必然伴生物,这决定了基督教天生具有全球扩张的基因,而扩张的实现还需要一些客观条件。在欧洲,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等使得欧洲势力的全球扩张得以实现。在美国,一方面是以“山巅之城”(the city upon the hill)为代表的美式救世主情节,另一方面则是防止美国过早走上全球扩张的孤立主义。美国的孤立主义始于乔治·华盛顿,并长期得到遵守,一战战胜国的地位也没能让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而珍珠港事件则让孤立主义在美国大幅度退缩。大部分美国人意识到,孤立主义并不能保证美国的安全,美国有必要主导全球集体安全体系的构建,以保证世界和平,进而切实保护美国的安全。这解决了美国领导世界的主观意愿问题。
客观因素方面,二战前,以“十四点建议”为代表的一整套美国外交理念尚未取代欧洲人主导的近代外交理念,欧洲式的外交理念依然是全球的主流,其主要特征包括:帝国理念、正统主义、大国协调、欧洲中心、秘密外交、殖民地体系、炮舰外交。
历史地看,17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是新教国家集团与天主教国家集团之间的宗教战争,由此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带来的主权理念,要害在于赋予一批国家信仰新教的自由,“教随国定”等原则获得承认。这标志着欧洲从神权时代步入君权时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主权国家时代。拿破仑战争的划时代意义在于,用“主权在民”的理念取代“主权在君”的理念,唤醒法国人的民本意识,从而把波旁王朝治下缺乏认同感的普罗旺斯人、布列塔尼人、勃艮第人、洛林人等等塑造为“法兰西人”。“法兰西民族”由此成型。拿破仑战争的巨大成功使得“民族国家”理念在欧洲生根、发芽、扩散,推动欧洲形成“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体系”。通过几波民族主义浪潮,全球越来越多的地方以“民族国家”的身份独立建国。美利坚联邦就是民族理念的第一批受惠者。普鲁士王国境内则诞生了强调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文化民族主义”,它唤醒了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邦联)境内各邦人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战后,“民族国家”成为全球现象,世界进入了“民族国家体系”时代。
美国的工业产值在1894年(当时还没有GDP这个概念)就成为世界第一。但在二战之前,领导全球机制的是欧洲几大国,全球教育与科技中心依然是欧洲,经济上美国相对于欧洲的优势还不够大。美国的军事实力同样如此,以海军为例,1922年《五国海军条约》规定的英美日法意五国主力舰吨位比是:5:5:3:1.75:1.75(按照吨位计算则是52.5万吨:52.5万吨:31.5万吨:17.5万吨:17.5万吨)。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构筑的全球殖民体系控制着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与人口。
两次世界大战不但摧毁了欧洲领导世界的能力,也使得欧洲丧失了领导世界的正当性:自诩文明、富裕的欧洲,其主要国家之间竟然以总体战的方式互相摧毁,还发生种族灭绝行为。这昭告世界,工业革命、民族主义与帝国野心已经把欧洲变成了全球最野蛮的地区,欧洲式世界治理体系彻底失败。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效法欧洲外交理念的典型例子。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老欧洲的帝国理念、大国协调、秘密外交、炮舰外交、殖民地政策也成为日本效法的对象,并以“脱亚入欧”化解“欧洲中心”,以“黄种人代表、打败俄罗斯帝国的大日本帝国”身份化解“正统主义”。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再次验证了欧洲外交理念的过时与欧洲式世界治理体系的失败。
一战摧毁了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也削弱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却让大英帝国领土扩张到极限,维也纳体系下的大国均势宣告终结。基于凡尔赛和约的国联是维也纳体系的余声与回响,但英法主导下的国联力量非常有限,原因有二:实力最强的美国游离于国联外:“欧洲宪兵”俄罗斯帝国解体,取代俄罗斯帝国的苏联奉行与西方不同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担任国联常任理事国的时间只有五年(1934-1939)。因此,国联连意大利都制约不了,更不可能约束住矢志扩张的日本。
二、美国领导能力的构建
二战严重地削弱了英法两国的实力,德国与意大利成为战败国,“亚洲优等生”“大日本帝国”惨败,苏联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成为军事强国。美国则成为世界的兵工厂,并为同盟国提供经济支持。二战结束时,美国GDP占世界的56%,工业产值占世界的40%,外贸占全球的三分之一,钢铁产量占世界的64%,石油产量占世界的70%,黄金储备占世界的73%(约200亿美元)。而曾雄霸世界经济100多年的英国,外债超过120亿美元,黄金储备仅100万美元。
军事方面,二战结束时的美国,总兵力达到1050万,各型舰艇10759艘,航母50多艘,并且独家拥有核武器。这时的美国,有能力与全球其他国家组成的“世界联军”作战并获胜。
二战中,全球特别是欧洲大量教育与科技人才向美国移民,使得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学术中心、教育中心与科技水平最高的地区。
外交理念上,以“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全面裁军、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民族自决”为主要内容的威尔逊主义,经过二战洗礼,大幅度取代欧洲人主导的外交理念并形成了国际政治中新的政治正确。《大西洋宪章》就是一个例子,连典型的帝国主义者丘吉尔也不得不接受威尔逊主义的一些内容(如不追求领土扩张、民族自决、机会均等)。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则成为美国在全球收割人心的一大利器。外交实践上,富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乔治·凯南、保罗·尼采等一大批美国精英把握时势,把美国的实力与潜能转化为美国对世界的制度化影响力。
三、二战后美国治理世界的方式
可见,直到二战后,美国才具备主客观条件替代欧洲大国充当世界领导国。二战后的美国因而得以联合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并吸纳其他文明圈国家,创建起主要基于国际制度的国际新秩序并延续至今:政治方面的联合国,安全领域的联合国安理会,金融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贸易领域的关贸总协定(及其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文化领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机制固然具有普世性的一面,但这些机制,美国通常是最大受益者,其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也明显大于其他国家,典型如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对重大事项的否决权。
而在军事领域,基于超强军事实力,美国搭建起双边或多边军事同盟体系:欧洲有北约,中东有“巴格达条约组织”(存续期为1955-1979年),东南亚有“东南亚条约组织”(存续期为1954-1977年)、美泰军事同盟、美菲军事同盟,远东有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大洋洲有《澳新美安全条约》(存续期为1951-1954年)与美澳同盟。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全球(最多时达到5000多个,现在依然有800多个)。军事基地与同盟体系不具有普世性,却为美国充当世界警察奠定了暴力保证。
与英国通过殖民体系来治理世界不同,美国只拥有少量的殖民地以及若干委任托管地,它主要通过国际机制来领导世界。但是,在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美国即使有心效法英国也难以做到。同盟体系与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则让美国得以用较小的成本控制全球大多数战略要冲,而不需要面对殖民地的副作用,包括管理殖民地的巨大成本。国际机制则为美国提供领导世界的正当性,并发挥美国的优势。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例,它让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美国不但避免了汇率风险,还可以享受铸币税。而生产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的美钞为美国从全球换来实实在在的货物与服务,加上巨大的美国市场,使得各国都愿意以低廉的价格向美国出口商品,美国人因而得以独享“优质低价”的商品与服务。科技与教育优势既为美国吸引全球人才,也让美国在科技、制造业、服务业领域保持优势,而基于自由贸易理念的关贸总协定与世贸组织,长期以来也有利于美国优势的发挥,特别是在服务业(金融业、信息技术业)与先进制造业领域。
四、美国相对衰弱的历程
美国的优势地位并没能长久地保持,特里芬难题(编注: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同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时,有可能造成国内短期经济目标和国际长期经济目标的利益冲突)决定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做法难以维持。石油危机促成美国在1971年放弃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调整是为了应对外来压力,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来自美国内部。华尔街制造的金融危机殃及全球后,美国自身通过量化宽松实现了经济率先复苏,其他国家则不得不为摆脱危机而苦苦挣扎,欧洲五国(PIIGS)是典型代表。这意味着美国不但无法充当世界经济的稳定器,而且成了世界经济不稳定的根源。政治与安全上,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与反恐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则让美国在全球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声望大跌,并引发对美国的新一轮仇恨。
冷战刚结束时,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意气风发,认为自己是新的罗马,具有拯救世界的实力与使命。但不过短短十多年,美国自身就成了世界经济与安全领域的“麻烦制造者”,对国际机制的影响力明显下降,继续领导世界已经力不从心。经济上,产业外移、过度依赖服务业使得美国国内中产阶级与下层人收入下降乃至失业。
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实力与全球影响力显著提升,欧洲谋求“独立”的意愿显著增强(希拉克与马克龙青睐的新戴高乐主义是典型)。
五、美国对相对衰弱的回应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开始了战略调整。先是奥巴马主义,其主要内容是:在全球施行战略收缩,减少对国际组织的支持,减少全球的军事介入,把军事安全的重点向亚洲转移,推行“再工业化”以重振制造业。接着是特朗普主义,这是一种新孤立主义,强调美国本土与美国人的利益至上,主张减少国际安全义务,让盟友与伙伴国更多地承担安全责任并提供资金支持。为达到目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不惜对盟友与伙伴国逐一施压,不断退出一些国际机制、放弃一些国际承诺。结果是,盟友、亲密伙伴国与美国的关系变得疏远,不再认为美国是可以依靠的盟友与伙伴。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上台后,内政外交上有意从特朗普的“打压对手为主”转向“提升自己为主”,但内政上大致延续了特朗普的政策,外交上则有一些调整,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缓和与盟友、伙伴国的关系,重返一些国际机制(如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但“减少国际干预、让盟友与伙伴国承担更多责任”的原则依然如故。
另一方面,构建不同类型的“新西方国家俱乐部”,以打压中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匈牙利、委内瑞拉、古巴、柬埔寨、缅甸、朝鲜等等不受美国待见的国家。
这在对华外交上有典型表现:战略上,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系统性挑战”,“来自不同文明的竞争对手”;战术上,主张用全政府手段对付中国。为此,在军事、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构建排除或针对中国的俱乐部(如美日印澳四方机制,蓝点计划,印太经济框架, G7全球基建计划);经济上,公然违背其一贯主张的市场经济规则,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上市与运营(如对TIKTOK),特别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用行政手段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如华为),并强迫盟友采取类似的政策;科技教育上,从芯片制造、学者交流、留学生所学专业等方面,对中国进行限制;在派驻对方国家人员数量、活动权限上要求与中国“对等”。安全上,鼓动北约成员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派军舰到台湾海峡、南海“巡航”。
美国属于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国家,具有强烈的救世主情结,体现为“山巅之城”信念、普世价值观执念、二元对立思维。美国精英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真正认识到:中华文明拥有不同于基督教文明的天下治理理念,具有世俗性、地区性、包容性、无外性等特征,这是中华文明能不间断维系几千年的主要原因。一神教世界的宗教战争是中华文明所难以想象的,中华文明也不具有全球扩张的基因与历史条件。在文明竞争时代,中国致力于实现的中国梦,实际上是一种文明复兴梦,这在多文明竞争时代是普遍现象。一种文明主导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多个文明“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实属必然。
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美国外交两大偏好,二战后国际主义占了上风,而现在,则在往孤立主义回摆,虽然不大可能整体上回归到二战前的状态,但会在一些方面明显偏向孤立主义,从而导致其不愿意也无力在国际上发挥二战后的影响力。从文明竞争的视角看,新教-天主教文明的全球影响力(文明力)在下降,美国作为新教-天主教文明的代表性国家,其文明力也在相应地下降。这既是必然,也是美国主动适应的过程与结果。
六、美国正在变成“红脖子泥瓦工”
综上可知,从主观上看,美国已经完全没有了超级大国的自信,也没有了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从客观上看,美国变得凡事计算利益得失,不愿意在必要时为国际事务承担兜底的责任(last resort),而是要求乃至迫使其他国家尽可能多地分担责任(典型如让英国牵头组建驻阿富汗的多国部队、让英法牵头推翻卡扎菲的行动、迫使盟国增加军费开支与美国军事基地开支的分摊比例)。这已经不是一个世界领导国应有的做法。这或许是因为,美国意识到了时代的变化,世界正在从大国竞争的时代走向文明间竞争的时代,全球化正在被各个文明的内卷所取代,承担世界领导不但成本高昂,也越来越难以做到。
因此,美国主观上不愿意、客观上无能力且不被接受继续承担领导世界的角色与成本。美国的文明影响力在下降,这是一个主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此,美国现在愿意、也有望做到的是:为自己与小团体谋利益,首先是本国的利益,其次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利益,再次是盟国的利益,又次是紧密伙伴国的利益。一般伙伴国的利益已经无暇顾及(世贸组织成员国是典型)。而比较疏远的伙伴、竞争对手与敌人,都是可以打压的对象。文化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美国热衷于树立对手、构建小院高墙,其深层原因在于基督教一神论价值观:把人分为教徒与非教徒,教徒是上帝的选民,对非教徒则必须通过软硬两手加以同化或者打压乃至消灭,因此强调二元对立。这与中华文明构成鲜明对比:强调不同族群与文明的和而不同这一根本特征,主张不同族群与文明的共存与互鉴。
世界上不认可美国领导权的国家也越来越多,除了上述不受美国待见的国家外,还有许多伊斯兰国家,特别是在中东北非地区。即使是北约成员国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公开倡导与推进欧洲的战略自主。
整体而言,美国表现得越来越不像一个世界领导国,而像一个普通大国。在全球事务中,已经难以如既往般充当领导者(leader),而是一个觅食者(forager),充其量一个协调者(coordinator)。对盟友与紧密伙伴国来说,美国是被动的协调者和主动的觅食者;对全球事务来说,则是消极的协调者和积极的觅食者。据此,有理由认定,美国正在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积极推手,变成热衷于构建小院高墙的红脖子泥瓦工(a mason with red neck)。
(本文发表于“澎湃新闻”2022年1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