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互联网的诞生,赋予研究者大量想象空间。从去中心化、扁平化到减少不平等,从话语空间拓展、媒介赋权到新公共领域建构、理性时代来临等等,研究者从多个层面研究了互联网及其社会影响。但是,互联网发展至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令人困惑的“互联网之问”。互联网本身是平等的,能促进减少不平等,但事实上互联网也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极化及撕裂;互联网能够促进宽容、理性的公共空间,但我们也看到了互联网上的民粹主义。
大量研究聚焦“数字鸿沟之问”(互联网扩大还是缩小了社会的不平等?)、“公共空间之问”(互联网促进了社会的开放还是社会的封闭?)等,各有各的道理。跳出这些问题和现象,从更加长期的趋势和结构出发,我们发现了另一个网络空间演进的规律,即互联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事实上取决于什么样的人在使用互联网。对于善用互联网的那一部分人来说,互联网带来了更为丰富、低成本的知识体系与更好的发展机会;对于开放、理性的那一部分人来说,互联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公共表达空间和公共交往领域。事实上,上述两类人在整体人口中是偏少的。在互联网发展早期,这种现象并不明显,但随着用户规模扩大,用户群体下沉,以及所谓的“互联网红利”的减少,网络人口结构特征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网络用户认知与观念的差异性逐渐扩大。
不同于美国在跨入互联网时代伊始就拥有大量使用人群——2000年时互联网渗透率已达到52%(Pew,2000),中国同期上网用户人数约为2250万人,仅占当年国内人口总量的1.74%(CNNIC,2000)。纵观2000年至2019年的美国互联网使用数据可以发现,美国的互联网人口始终是学历越高,互联网使用率越高(Johnson,2021),其网络空间长期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作为关键群体,掌握着核心话语权。相比之下,中国的互联网人口结构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CNNIC近20年历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数据显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互联网人口占比,2000年为84%,2003年将为57.2%,2014年降至21.4%,2020则为19.8%。
中国网络空间正在经历深刻的底层化过程,表现在底层价值取向成为网络空间的关键立场,底层群体成为网络空间的关键意见群体,“底层客体性时代”向“底层主体性时代”的转变,成为理解网络空间演进方向的新视域。与此同时,多级信息生产、平台商业逻辑与网络空间底层性的形成,有利于我们从机制的层面,探索网络舆论场意见表达的时代特征与网络空间深层重构的长期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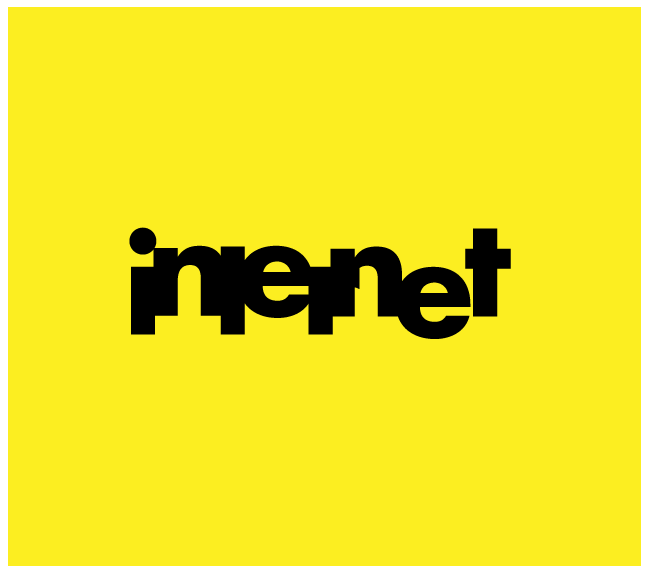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当前有关网络空间演进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多聚焦在技术、政治、监管、资本等力量与网络空间的相互作用(Castells,2010;Hepp,Hjarvard & Lundby,2015)。例如,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管政策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互联网平台、重要传播节点以及一般网络用户的行动模式,国家采取硬件基础管理和平台治理等多种手段对网络空间进行治(King,Pan & Roberts,2017),可以改变网络空间的主要话语生态(Tong & Lei,2013;Han,2015;桂勇等,2018);商业竞争驱动不同平台占据不同的细分市场,出现不同定位的社交媒体平台,进而影响网络表达;商业资本通过推荐系统、“水军”、机器人、虚假评论等方式渗透进网络空间的方方面面,影响人们的社会认知(Damm,2007;Yu,Asur & Huberman,2015;罗教讲、刘存地,2019);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算法向用户推荐有针对性的信息,从而带来平台的算法审查和特定偏向(方师师,2016),等等。
以上研究虽然在多元力量影响互联网的路径中部分展现了网络空间演进背后的规律和特征,但大部分研究结果无法解释引言部分提到的一些深层次的网络空间现象和问题,亦无法以一个相对系统的解释框架对中国互联网的长期趋势作出阐释。技术、政治、资本等种种影响网络空间走势的动能,最终都要汇聚到“人”(网民)的身上。中国互联网人口结构的变迁、演进,可能成为理解中国互联网发展规律的重要切口。

已有部分研究关注到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文化资源、群体素质、人数规模等差异性因素显著影响着普通网民在互联网上的互动表达及其分化(Rains et al.,2017;Fu& Chau,2013;赵云泽、韩梦霖,2013;邵春霞、彭勃,2015;郑雯等,2017);网络极端情绪人群的类型与年龄、职业和教育水平等用户特征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桂勇等,2018);相关研究虽然从丰富的面向探讨了相关问题,但相对整体性的分析框架远未形成,亦缺乏历史的、动态的、随时间演进的研究视角。
笔者认为,底层在互联网人口结构中的重要演变趋势及其对网络空间演进的深刻影响,介乎结构、叙事与机制之间,值得高度关注。虽然“底层”本身的概念存在模糊性,在传统社会分层理论中并非明确指向某个阶层、某种职业和身份,而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元维度建构的复合型概念,但是就底层社会的基本样态来看,存在一些基本共识,比如生活贫困、经济诉求为主、持续性发展能力弱等(文军、吴晓凯,2015)。当下国内研究指称的中国底层群体/底层社会,主要由贫困的农民、进城务工者和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构成(孙立平,2002)。这一社会群体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蕴含着社会结构、社会层级方面的“高下差异”,与“中间阶层”“精英阶层”等概念相对,在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职业身份与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特殊指向性。不同于文化概念中的“大众”,底层研究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及其权利的争取。在这一学术脉络下,互联网与底层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媒介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关注、底层群体通过互联网赋权争取权益等方面(许向东,2008;李红艳,2016),对底层群体的观念认知、媒介接触与使用、网络素养状况、情感和生活行为等有一定关注(方晓红,2002;郑素侠,2013;陶建杰,2016)。
互联网在底层群体集体赋权(collective empowerment)以及构建弱势群体集体表达空间(deliberative space)等方面发挥作用(Qiu,2016;Yin,2018 ;Sun,2009、2014),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中被不断检视(Mehra et al.,2004;Mitra,2010;Jue,2016)。由于长期囿于“底层关注”“底层发声”的范式,既有研究多将底层研究限定在冲突性的关系结构中,遮蔽了中国底层群体和底层社会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自上而下的视角将底层作为社会弱者看待,忽视了底层对媒介生态的反向建构。事实上,在被互联网与新媒体赋权的过程中,中国的底层群体正以愈加成规模的表达声量和行动力,影响到网络舆论走势及其背后的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思潮。在持续演进并重构的过程中,底层群体成为影响网络空间权力结构、力量格局、价值取向与运行逻辑的关键要素。从更大的政治社会图景看,底层作为网络空间中的重要变量,既受到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影响,也反过来影响着网络舆论场,成为引言所述的理解中国网络空间多重问题的切入点。底层在被媒介赋权的同时,亦激发了社会变革特别是互联网演进的原生动力,它对社会结构、媒介环境、网络生态的反向影响正在加速凸显。
本文跳出底层研究的“媒介赋权”等传统路径,将底层看作具有显著、稳定、成熟的网络表达特征和群体价值属性的关键群体,以“底层主体性”的学术视角研究中国网络空间底层化过程中的网络表达、社会情绪、社会思潮、价值取向与平台逻辑,尝试描绘中国网络空间“底层主体性时代”的表征、机制及其发展趋势。
作为西方近代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对“主体性”比较流行的界定如下:主体性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目的性等主体属性(陈海平,2006),其核心内涵是主体凭借和发挥其自身力量,通过对象性活动,按照为我的目的和倾向去把握客体(沈晓珊、李林昆,1991)。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推动本文对主体性概念的使用,即主体性主要显示出主体在主客体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和支配作用。
有学者指出,研究主体性首先必须区别两种不同的主体,一种是占多数且居主导地位意义的主体,主要从量的方面来划分,比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主体;另一种是主客体活动中的主体,与客体是一对矛盾,是辩证法的一对范畴(刘守和,1992)。本文建构的底层主体性,既是在量的层面占多数的底层主体,也是在质的层面能够作用于客观对象的主体。底层群体在网络空间与精英阶层、中间阶层交往互动从而取得主体性的过程,一方面,受益于互联网不断下沉使其在量的层面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底层通过其自身在网络舆论场的深度浸入,在实践层面发生了质的改变。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对网络空间进行机制性的重新建构,发展出底层自身的主体性。
与此同时,马克思交往实践观认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基础的交往实践活动本身蕴含着双重关系:其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其二是人与人之间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或主体间性(柴秀波,2011)。本文所讨论的中国网络空间进入底层主体性时代,也建立在这双重关系的讨论之上。底层主体性时代,既是讨论底层建构互联网生态环境所体现的主体性,也是他们在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交往实践中逐渐改造交往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发挥主要作用的主体性。底层、中间阶层、精英阶层等各类群体以互联网作为对象性活动的中介进行交往实践,发生交互关系的过程,也是底层在其中增强自身主体性力量的过程。
本研究将围绕以下两个核心问题展开。
(1)网络空间底层化如何从“底层客体性时代”走向“底层主体性时代”?
(2)如何理解底层主体性时代背后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