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拥抱“身份政治”的民主党?
面对着人口变动对选民构成的松动、选民内部不同群体的分歧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代际停滞,民主党极可能需要通过政党议程乃至政治生态的调整来适应新现实、应对新挑战。一方面,拜登所代表的“新民主党”和桑德斯所代表的“进步主义民主党”乃至激进派分别回应着持有温和保守立场的民主党支持者和受教育程度偏高的白人群体或年轻世代,一方通过经济政策主张的调整来整合另一方的难度较大。另一方面,面对着拉美裔人口以及选民持续激增且存在倒向共和党可能的现实,民主党就必须想办法复制上个世纪中叶吸纳非洲裔的成功,制造出新的对自身有利的关键重组。
面对选民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新局面,民主党目前看最有效的聚合路径即淡化相关政策分歧、转而彻底拥抱能够得到持有自由派立场的白人、持有温和保守派立场的少数族裔所共同接受的“身份政治”,进而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稳固的(或许是多数的)选民联盟。这就意味着,面对着共和党从1990年代的所谓“文化战争”到如今的“特朗普化”,民主党极可能需要相应地调整到与其争锋相对的“身份政治多元化”方向。在相关政策议程上,民主党要将较为宽容的移民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税收、就业、教育乃至福利政策作为至关重要的抓手,满足自由派白人群体的政治审美,也尽可能符合少数族裔的利益诉求,并以移民政策作为“楔子”来尽可能阻断拉美裔与共和党的走近可能。
这种拥抱“身份政治”的选择虽然可能平息民主党内部不同群体乃至派系的分歧,但却会彻底失去包括蓝领中下层在内的受教育程度偏低且有温和派立场的白人群体。换言之,“身份政治”将促使民主党倒置阶层逻辑和族裔逻辑的关系,即以族裔逻辑涵盖、容纳阶层逻辑,蓝领中下层群体随之被分解为非洲裔、拉美裔等少数族裔蓝领和白人蓝领,前者仍可被民主党的“身份政治”所稳固,但后者则会由于“身份政治”而进一步放弃民主党。进而,民主党不但会彻底失去新政以来的蓝领群体,而且也将在客观上继续强化“特朗普化”的共和党对蓝领白人的吸引。
虽然民主党仍可保持受教育程度偏高白人群体的一定选票,但拥抱“身份政治”所导致的另一个趋势可能是促使民主党的政治精英群体不同程度的所谓“非白人化”乃至所谓“少数族裔化”。一方面,非洲裔群体在2008年以来四次总统大选中的表现足以证明该群体更为期待非洲裔候选人。研究证明,在非洲裔选民整体上支持民主党的既定事实下,民主党非洲裔候选人可以极大提升非洲裔选民的投票率,但共和党非洲裔候选人却不具备此效果。这就决定了民主党人也越来越需要选择非洲裔面孔作为候选人,才能确保非洲裔选民能够以较高投票率巩固民主党应得的基本盘选票。从奥巴马到哈里斯,这个趋势已在总统政治层次被不断认可并强化,未来在其他层次的竞选中民主党也极可能重蹈覆辙、不得不特意提名非洲裔人选。另一方面,相比于非洲裔的投票率问题,持续激增的拉美裔所带来的则是更为支持谁、甚至会否较为固化地彻底倒向哪一党的问题。研究证明,一般情况下,大多数(84%)拉美裔选民会按照长期形成的党派归属投票,只有极少部分会不确定如何投票或由于特殊情况而跨党投票(各8% 左右);但如果有拉美裔候选人参与,拉美裔选民按照政党归属的比例会下降到40%左右,可能跨党者增长到26%,举棋不定者也升至34%。由此可见,虽然没有需要非洲裔候选人来稳固非洲裔投票率那么迫切,但在某些难以以党派归属完全取胜的情形下两党都有可能通过提名拉美裔候选人的方式来尽全力争夺选票。当然,就民主党内部的提名过程而言,与非洲裔选民在选举意义上更为聚合、更为强烈地支持非洲裔候选人不同,民主党倾向的拉美裔选民也会因为年轻代际等因素而支持桑德斯所代表的理念而非本族裔人选。2020年民主党总统初选中唯一的拉美裔参选人朱利安·卡斯特罗(Julian Castro)并未在拉美裔群体中获得优势,也正是由于此原因。同样,如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茨(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持有进步主义甚至激进理念的、属于新世代的拉美裔民主党人更容易在巩固本族裔群体支持的优势下得以脱颖而出。
事实上,在2016年民主党败选以来特别是桑德斯无法获得提名之后,民主党内部已逐渐形成了强调所谓“绿色新政”(New Green Deal)等激进进步主义理念的新派别即“正义民主党”(Justice Democrats),奥卡西奥-科茨就可算作其代表人物。该分支不但在2020年民主党总统初选中支持了桑德斯,而且还在2018年和2020年各层次民主党初选中多次提出支持人选,其中存在着较多的相对年轻世代的拉美裔或非洲裔人选。截止到2020年8月底,已有三位长期在任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在初选中失败,而将其挑落的挑战者均属于“正义民主党”,且其中两位为1970年代出生的非洲裔新面孔,足见其正在发挥着某种程度上类似当年“茶党”对共和党的作用。这也意味着,“身份政治”、激进理念与年轻世代等要素的组合,不但实现了“进步主义民主党”的历史性回摆,更可能代表着民主党整合与转型的新方向。
必须承认,民主党在政治精英层面上的“非白人化”或“少数族裔化”所导致的一定是两党政治的进一步“部落化”。事实上,2016年大选以及其后的事实已经证明,当蓝领中下层白人认为奥巴马及其民主党人制造出的所谓“族裔焦虑”已超越了“经济焦虑”之时,他们就不会再因为民主党的经济与福利政策而继续保持对其的支持,而是会转而倒向鼓吹“白人至上”的共和党。于是,演变中的党争极化与无法改变的族裔鸿沟正在高度重叠并发生剧烈共振,从而强化着美国两党政治更为难以调和的困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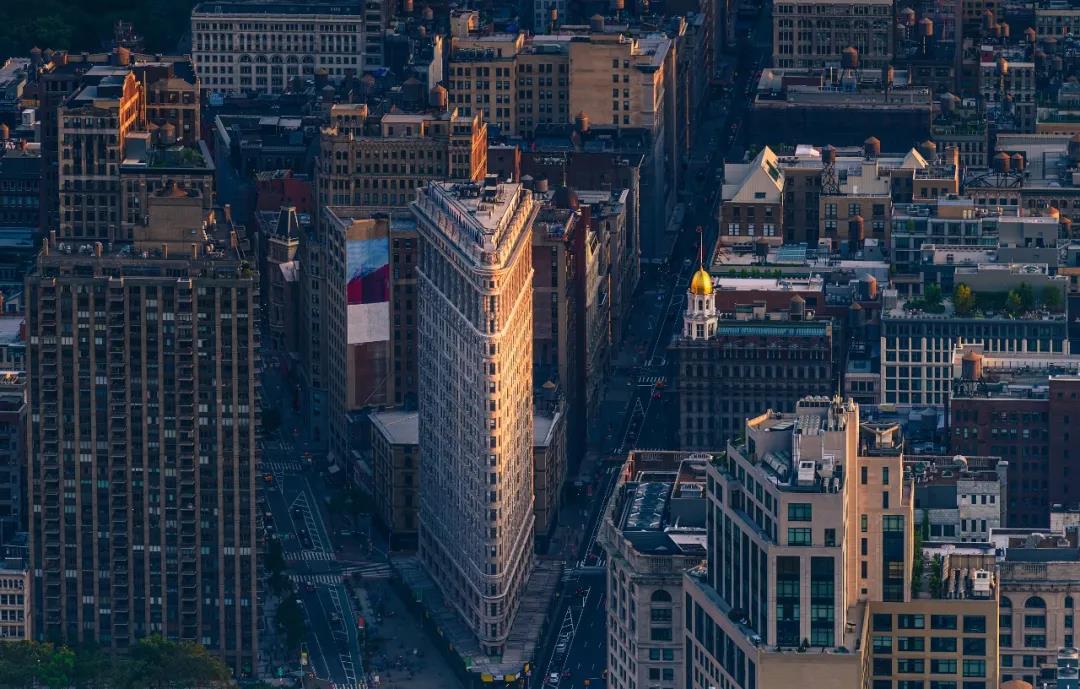
结语
2020年大选中拜登与哈里斯的组合可谓是民主党再次希望通过平衡与聚合不同利益群体而达成多数选民联盟从而谋求胜选的一次尝试。无论成功与否,这对于民主党而言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甚至,哈里斯的存在也在不断提醒民主党拥抱“身份政治”的未来。
虽然近年来民主党内部也出现了颇多更具包容性的呼声,比如希拉里在总统竞选期间的口号“团结更强大”(stronger together)或者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的那句“他们走向堕落低劣,我们要走向更高处”(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的经典表达,这些信号都试图将民主党置于一个致力于重建相互容忍与克制的高位之上,保持乃至重塑所谓“美国信条”,团结包括白人、少数族裔在内的全体美国人,进而跳出相互恶性否决与极端化的怪圈。但问题在于,在党争极化与竞选政治的客观压力之下,民主党如果固守更具包容性、甚至更为理想主义的政策议程,必将无法在现实政治中有效建构出足够胜出的选民联盟,其结果极可能是在多次选举失败之后还是会驶入与共和党“白人至上”相对应的“身份政治”轨道。这是美国政党政治在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徘徊,也是两个不同形态政党相互塑造的必然结果,构成了民主党不得不面对的悖论。
同样艰困的是,虽然同为“身份政治”方向上的操作,共和党所坚持的“白人至上”是从历史中走来的,是将这个国家带回已知的“故土”;而民主党所倡导的“身份政治多元化”却仍是一个试图平衡、聚合持续增长的少数族裔群体的新的“美国梦”,是尝试将这个国家引向从未见过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前预设的理想化“未来”只会强化某些人对“故土”的眷恋;而只有在人们充分认同“故土”已逝的时候,才会愿意共同努力去营造共享却未知的“未来”。
(刁大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