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社会主义浪潮之下,拜登也向左翼示好,如将沃伦、科特兹等人拉进不同政策工作组中担任要职,提出对富人征税,支持 15 美元最低时薪,在未来十年内投入7500亿美元支持医保,将医保的年龄门槛从65岁降到60岁,在未来四年内投入2万亿美元推动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重建,对年收入低于35000美元的家庭免除学生贷款等。有关举措消化吸收了不少进步派的主张。2020年8月11 日,拜登提名贺锦丽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此举显然意在借助贺锦丽的少数族裔身份和进步立场来团结党内左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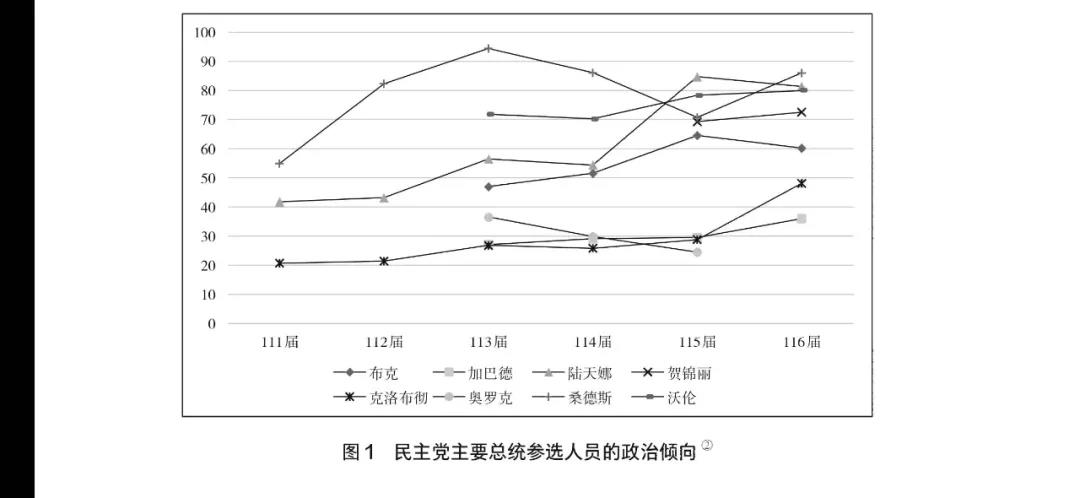
(三)民主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
民主社会主义的再度兴起,离不开相关组织从国会到地方选举的精心布局,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DSA)。过去数十年里,DSA一直默默无闻,属于不被主流接受的外围团体。但近年来,该组织成员数量激增,截至 2020年3月底,缴纳会费的成员超过 56000 人,在全美各地拥有近 200 个分支。
DSA 最主要的政治目标是将更多民主社会主义者送入美国政治体制,在政府内部推动变革。在 2018年中期选举中,超过40名DSA 支持的候选人当选州、县、市民选官员,其中两位成员当选国会众议员。2019年4月,6名DSA成员当选芝加哥市议员,总数占市议会总数的10%,被认为是"美国现代历史上社会主义者最大的选举胜利。"2019年 11月,20名DSA 支持的候选人当选为国家及各州、县市层面的民选官员。其中,哥伦比亚裔候选人朱莉娅·萨拉查(Julia Salazar)当选为纽约州参议员,7名成员在康涅狄格州各地胜出,以工人家庭党代表身份参选的肯德拉·布鲁克斯(Kendra Brooks)轻松当选费城市议员,成为过去百年来该市首位第三党胜出者。
DSA 最为重大的选举胜利,在于历史性地将两名女性成员——科特兹和拉什达·塔莱布(Rashida Tlaib)送入国会。2018年6月,名不见经传的科特兹,以"政治黑马"之姿击败有望接班佩洛西的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主席约瑟夫·克劳利(Joseph Crowley),赢得纽约州第14国会选区的民主党提名,这被《纽约时报》称为"过去十多年来民主党在任议员最为重大的失利"。2018年11月,28岁的科特兹成功当选史上最年轻的国会女议员。科特兹上任以来,以其出众的口才、犀利的风格赢得大量年轻人追捧,并推出"绿色新政"等政策,迅速成长为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青年领军人物。"科特兹现象"成为"桑德斯现象"之后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高潮。
二、民主社会主义此轮兴起的原因
民主社会主义在 2020 年大选中的卷土重来,本质上源于国内政治经济状况恶化的长期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民众对自身境遇未见显著改善的不满情绪仍在蔓延,尤其是年轻选民越发对特朗普四年执政表现及民主党建制政治感到愤怒与失望,寄希望于通过自身力量革旧立新。
(一)为公正而战∶ 民主体制痼疾亟待革除
在 2020年4月初中止选战后,桑德斯在《华盛顿邮报》上发文表示,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但却处在大规模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时期,对靠薪水过活的一半美国人、4000万贫困人口、8700万无医保或没有完全医保的民众,以及 50 万无家可归的百姓来说,这种现实没什么意义。当下我们正处于双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崩溃之中,必须重新审视美国社会的一些基础,理解他们为什么让我们失望,为一个更公平、公正的国家而战。"对不少民主党人来说,全球化、去工业化和大集团政治控制之下的美国,与桑德斯所描述的垄断资本主义颇有相似之处。
首先,经济不平等是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首要纠偏对象。民主社会主义者对美国的最激烈批评,在于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和机会不平等。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从1979年到 2015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工人周薪仅增加了10美元。同一时期,公司利润、股票价格及高管薪酬则飞速上涨。在过去四十年里,美国工资收入的大部分流向了收入最高的阶层。自 2000年以来,在收入最低的10% 人群中,周薪仅增长 4.3%。但是,收入最高的前10% 人群的实际工资累计上涨15.7%,达到每周 2112美元,大约是收入最底人群的五倍。若以购买力计算,普通人的平均时薪相当于 1978年的水平。当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民众,与处于顶层的1%或0.1%人群之间产生难以逾越的经济鸿沟,那么"被遗忘"的愤怒与不满情绪必然激化。征收富人税、免费大学教育、全民医保、取消学生贷款、提升最低时薪等为民众许诺大量福利的主张,触及民众最为核心的利益关切,很容易快速积累大量支持。用桑德斯的话说,"(民主)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归国家所有,而是创建一个国家和世界,所有人在其中能拥有体面的生活。"
其次,政治体制衰败助长意识形态的剑走偏锋。进入21世纪,两党政治"两极化"不断加剧。到奥巴马上任后,政府陷入漫长的僵局循环,"否决政治"取代宪政设计中的"协商和同意"理念成为主流,利益集团的巨大影响更阻碍了代表更广泛利益的政策的出台,导致立法决策极其低效、碎片化,政治机构的公众信任度不断走低,政治体制不可避免地发生衰败。当政治越发沦为少数人的游戏,决策的自利倾向便显著上升。以特朗普胜选为标志,两党对固守所谓"基本盘"的执念史无前例地强化。处于意识形态光谱两端的右翼保守主义和左翼民主社会主义,迎合了基本盘对建制派统治的失望与不满情绪,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广大年轻选民更倾向于支持左翼政策主张,希望通过变革理念和制度来根除美国政治的毒瘤。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抓住这种心理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
再次,阶级与文化隔离的加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吸引选民的主要方式,在于聚焦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同时将其升华至道德和精神层面,简化为政治上正确、连保守派都难以反驳的声讨∶ 在一个富足发达的国家,却存在大量穷困潦倒的人民,这应该忍受并且在道德上可接受吗?民主社会主义者希望传递的信息是∶"美国梦"越来越遥远的根源在于阶级和文化的隔离。经济不平等加剧了阶层分化∶ 中产阶级受挤压,工人阶级穷困潦倒,美国原本相对畅通的社会结构日渐僵化。普特南认为,从邻里、教育和婚姻三个层面看,过去四十年间已经出现了基于阶级隔离的普遍分裂。当家庭开始分裂、社区逐渐消散、宗教传统淡化,个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在社会群体中的疏离感与孤独感与日俱增,民主社会主义便成为许多人情感和道德上的某种寄托。因为后者所提出的,不完全是为社会带来免费的公共政策和服务,更赋予了一项使命——一种表达美德的方式,以及为实现许多人认为有意义的目标而团结起来的理由。大概基于这个考虑,桑德斯用较为模糊的逻辑来定义其眼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根本上是相信"不公正是不对的,平等是好的,团结是必要的"。这种对阶级隔离的抨击和对文化淡漠的同理心,容易与普通民众产生共鸣,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社会主义的"颠覆性"色彩。






